
9月19日傍晚,西藏日喀则江孜县热龙地区,海拔55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脊线上,火焰腾空而起。一场由户外品牌始祖鸟联手艺术家蔡国强打造的“艺术烟花秀”——《升龙》,在轰鸣声中划破雪域寂静。
然而,这场以“敬畏自然”为名的表演,却因可能对脆弱生态造成破坏而引发轩然大波。次日,品牌与艺术家删除了宣传视频。
9月21日凌晨,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就此事发布情况通报称,日喀则市委、市政府已成立调查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,后续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。
通报发布后,蔡国强工作室与始祖鸟品牌相继公开致歉,并表示如烟花对环境有影响愿全力补救。9月22日,已有环保专家抵达现场进行生态修复。有媒体报道称,经专家初步判断,遭到破坏面积不大,正在清理现场的紫铜、塑料桶等。
艺术与生态的碰撞,暴露出高原环境保护的深层困境。
烟花燃放现场:味道刺鼻,辣眼睛
“燃放时像地震一样,我整个人都在抖。”日喀则定日县村民陈铭(化名)回忆。作为当天活动的接送司机,他目睹了烟花秀的全过程。
9月18日晚,陈铭接到通知第二天要去接人。9月19日清晨5点,陈铭起床前往日喀则市某酒店。等待的一个多小时里,他询问酒店负责人缘由。“他只是和我说,有一个投资了很多钱的项目。到了现场后只可以拍照,不能发到网上。”陈铭回忆。
8点多,陈铭带着2位负责人和40名厨师启程。跟随陈铭出发的,还有两辆货车。
车队开了近3小时才抵达热龙山山脚。陈铭看到,路边已停了很多车,现场十分忙碌,有许多扛着摄像机的工作人员,还有无人机,有村民在搬东西。村民们说,他们是被村长叫来搬座位的。村长向他们承诺有工资,但没有告诉他们具体是什么活动。
下午5点左右,烟花秀正式开始。陈铭回忆,烟花每10分钟左右燃放一次,一共燃放了约4到5次,每次颜色都不一样。烟花从山顶蜿蜒到山脚,燃放时,声音和震感都非常大。
陈铭距离烟花燃放点约三四公里,但他仍能感到,烟花燃放后,“空气中的味道非常刺鼻”,“眼睛辣辣的”。
 烟花燃放时产生的烟雾巨大。受访者供图
烟花燃放时产生的烟雾巨大。受访者供图
直到这时,陈铭才知道,这是始祖鸟和蔡国强联合创作的一场烟花秀。“他们弄得太神秘了”,陈铭不认识“始祖鸟”,一度将之错误地称呼为“鸟族”。
除本职工作外,陈铭也是一位藏区牧民。陈铭在现场看到,烟花燃放后掉落了许多细小残渣。“高海拔本来就不容易长草。这样燃放烟花,那块地多久很可能长不出草了,那牦牛吃啥?牧民咋办?”陈铭表示,燃放烟花的地方,距离农民们种青稞的农田仅300多米。
在现场,陈铭没有看到动物出没。“这样的震感,连人都受不了。动物估计直接被吓跑了。”
 烟花秀区域距离青稞地和卡若拉冰川不远。受访者供图
烟花秀区域距离青稞地和卡若拉冰川不远。受访者供图
让陈铭感到气愤的,不仅是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有可能遭到破坏,还有对当地习俗的不尊重。
在藏民的眼里,雪域是纯洁无瑕的一片圣地。每次陈铭带游客去珠峰脚下都会嘱咐游客,“不能喊太大声。”
陈铭表示,燃放烟花的地方距离卡若拉冰川仅5公里,而卡若拉冰川被当地藏民称为“神山”。曾有一部电影取景时,为呈现真实场景,剧组在卡若拉冰川上炸出了一个三角形缺口,人为制造了一场雪崩,画面在电影里呈现不到20秒,但缺口却至今还未“愈合”。
在陈铭看来,这次的烟花秀,和当年的电影一样,打扰了山神,侵犯了神圣。
生态破坏不可逆
夏尔巴向导旦增认同陈铭的担忧。他对西藏当地的生态环境较为熟悉。旦增介绍,直至今日他攀登了32座近6000米海拔的雪山,“还有数不清的5000多米的海拔的雪山。”
旦增了解到“始祖鸟烟花秀”的新闻后十分震惊,认为如此大阵仗对雪山冰川的伤害是巨大的、不可逆的。“可能导致那片土地十几年内都不会再生长。”
面对公众质疑,主办方曾回应,该烟花项目已通过国际奥委会及日本、欧美等多地燃放验证,确认其污染物排放符合环保标准,燃放等级为V级(最低风险),噪音与光污染显著低于常规夜间焰火,力求最大限度减少对环境与公众的干扰。
在生态保护方面,主办方表示已实施全链条管理方案:燃放前转移牧民牲畜至安全区域,并通过放置盐砖引导鼠兔等小型动物远离燃放区;燃放后立即清理残留物,并委托专业机构对草甸和农田进行科学修复,避免遗留生态风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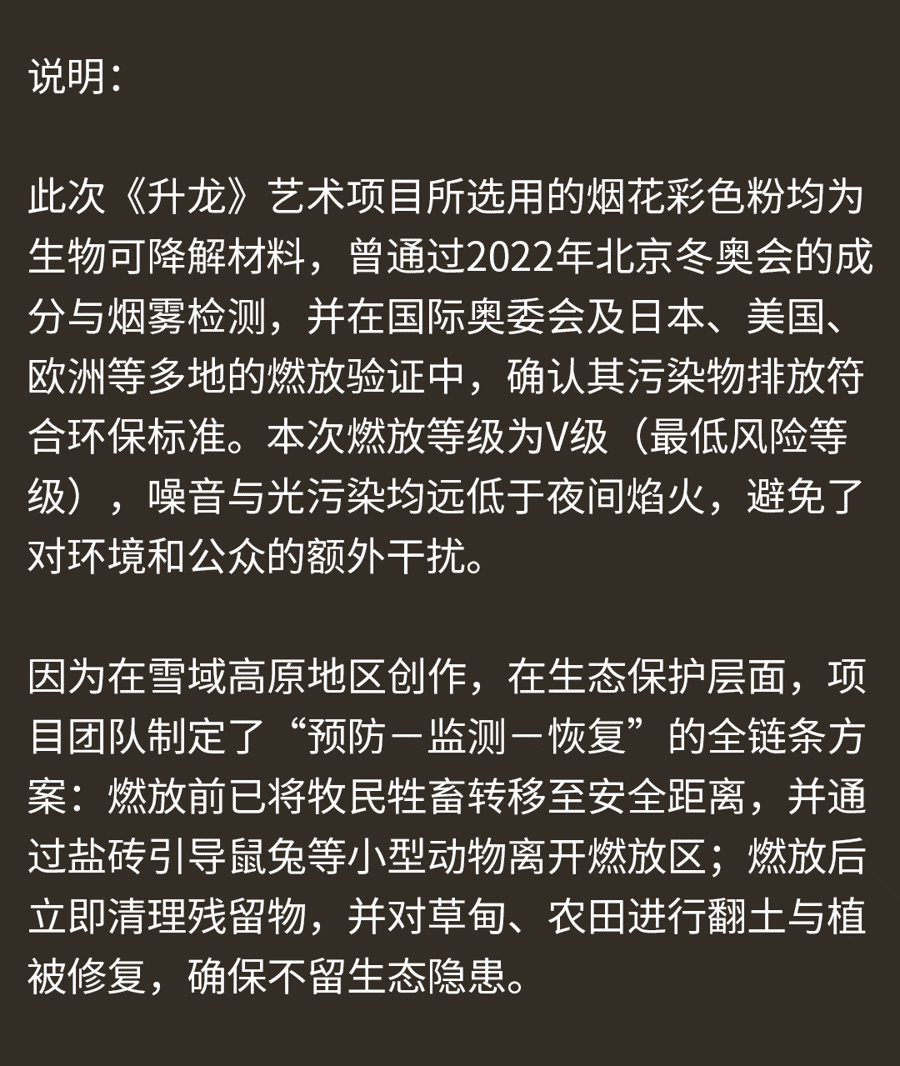 主办方的说明。
主办方的说明。
然而,在喜马拉雅这类生态极度脆弱的高原地区,上述措施是否真正有效,值得深入审视。
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张强弓在论文中指出,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多为海洋型冰川,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。该区域生态脆弱,冰川加速消融已带来一系列连锁影响,亟需科学应对。
“空气侠”发起人赵亮基于十余年环保一线经验指出,烟花燃放过程中产生的烟雾、粉尘及彩色烟花中的化学颜料,短期内会对空气质量造成冲击,其可降解性与毒性也存在不确定性。长期来看,未清理彻底的残留物可能持续释放有害物质,燃放产生的热量亦可能加剧冰川融化,对高原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损害。
赵亮进一步解释,青藏高原特殊的高海拔、低温、低氧环境,会导致烟花残留物的降解和扩散速度显著减缓。烟花中的所谓“可降解材料”在高原环境下分解效率极低,残留粉尘与颜料可能长期滞留空气或地表。
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顾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强调,“可降解”不等于安全,更不能成为高原环境下的“免责牌”。高原微生物活性低,玉米淀粉基彩粉等非原生材料的降解周期缺乏实验数据,其中染料的降解过程与生态影响更是未经验证。
青野生态负责人刁鲲鹏从生物与植被的角度提出批评:烟花巨响严重惊扰鼠兔等小型动物,所谓“盐砖引导”并不符合其习性,反而可能造成惊吓或死亡。同时,燃放装置布设直接破坏草毡层——这是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关键结构,一旦损毁,易引发土地退化,严重影响野生动物栖息。
对于事后修复,刁鲲鹏建议避免翻耕等二次干扰,草毡层破坏后几乎不可自然恢复。残留的彩粉可以通过物理吸附清理,防止化学染料渗入土壤水源;已污染区域则需专业环境机构介入,采取科学手段进行长期治理。赵亮同样强调,高原生态修复必须依靠专业团队,进度应公开并接受社会监督,而不是简单“翻土”就算修复完成。
“环境评估”在哪里?
日喀则市生态环境局江孜县分局一位负责人此前向媒体表示,此次活动已在生态环境局备案,手续合规。因烟花采用“环保材料”,未进行环境评估,仅经乡、村、县三级政府同意即获批。该负责人称,政府曾多次开会研究选址,评估周边野生动物情况,最终选定区域不属于生态保护区,且周边无人居住。
然而,烟花虽已熄灭,追问却不应停止。在高原举办大型烟花秀,显然面临着可预见的生态破坏。审批是怎么办下来的?监管又在何处?当地生态环境局“已备案,无环评”的答案难以服众。
针对活动方以使用“环保材料”为由而未进行环境评估的做法,刁鲲鹏表示质疑。他强调,在青藏高原这样生态脆弱的地区,任何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活动都必须进行严格的环境评估。
“环境评估不仅是对材料本身的化学残留进行评估,还应涵盖爆炸产生的冲击、噪声、微粒对空气质量的瞬时影响,以及施工和人员活动对地表植被的物理性破坏等多个方面。”
刁鲲鹏特别提到,我国对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保护有着严格的政策要求。2023年出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》明确,青藏高原保护范围包括西藏自治区、青海省的全部行政区域等。其中指出:“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应当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、保护自然”“坚持生态保护第一”等。
此前,北京盈科(上海)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、盈科全国碳达峰碳中和法律专委会主任刘新海向媒体表示,虽然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未明确将烟花爆竹燃放纳入强制环评范围,但青藏高原作为“生态敏感区”,应参照《西藏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〉办法》,对可能影响生态系统的活动从严管理。
与此同时,江孜县分局所说的“乡、县政府同意即可”,看似流程完整,但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,可能影响生态的活动都需征求专家和公众意见。甘肃政法大学教授冯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》都已有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,当地政府其实无权审批此项活动。
刁鲲鹏认为,此次活动中地方政府可能因信息闭塞或急功近利的心态,未能充分履行环境评估的职责,这既是地方政府的失职,也是活动方的责任。
在谈及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时,刁鲲鹏结合自身实践经验指出,他所在团队曾在当地开展野生动物监测与生态保护项目,每次活动均需经过严格审批流程,包括对当地动植物影响的评估及预防措施设计。他特别提到,此前在四川、甘肃等地组织的越野跑活动中,主办方需提供对当地生态无干扰的证明,并由专家进行环境评估论证。这一流程不仅是为了约束活动可能造成的生态破坏,也是通过专业意见指引主办方优化方案。
基于丰富的户外经验,旦增认为,问题的核心仍在于管理。他对比了西藏不同地区的生态现状:在219、318国道沿线一些管理松懈的区域,游客众多,垃圾遍地,他亲眼目睹库拉岗日北麓冰川一年退缩二十余米;而在隆子县扎日圣湖措嘎,因有文旅局局长带头清理垃圾、要求进入者签署环保保证书等严格措施,生态环境良好,甚至孕育出上万朵雪莲花。
 扎日圣湖措嘎地区的雪莲花。受访者供图
扎日圣湖措嘎地区的雪莲花。受访者供图
9月22日,据内部人士透露,目前自治区已就此事开会,形成调查组,调查完后会发布通报。
但生态破坏的滞后性意味着,真相可能需要数年评估才能浮现。
(实习生黄佳瑜、胡婧懿、孙怡洋对本文亦有贡献 )
鸿岳资本配资-国内股票配资-股票的杠杆交易-中国股票杠杆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